值得注意的是,梁文福横跨文学与音乐两个领域。文学方面,他创作散文、小品、诗、寓言、小说等多种文类写作。音乐方面,他是1980年代新加坡音乐新潮“新谣”的代表歌手,多年创作的音乐让他闻名国际,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圈的知名人士。
张悦然,应该不算是新华作家,但曾经在新加坡场域生活过,在新加坡写了她的著名长篇小说《誓鸟》。在新华文学史上,张悦然无足轻重,但她的跨国行旅在离散语境里勾勒一个南向北回的弧度。
虽然深情地缅怀传统华人文化的流逝,梁文福却也热情地拥抱杂糅的现代性。
可以预见,这类的文学国民,甚至国民文学,将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时光如白驹过隙,现在新华文学的国民性,已经远离中国,深深在脚下土地翻耕版图,翻建大厦。
5月4日:同日异地
后来的历史叙事,更是将五四运动扩大时间范围,包括从1915年中日签订《对华二十一条》至1926年北伐战争的这段时期,也包含新文化运动。在“反传统、反儒家、反文言”的国族觉醒与文化决心当中,陈独秀提倡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马克思主义,胡适则推动白话文运动。
更加需要一提的是,梁文福的作品包含多元文化元素,尤其在音乐的创作上。例如他作词作曲的《新加坡派》,寓意显然是新加坡文化的杂糅性,曲风吸纳了台湾的、香港的、马来的、美国的等音乐风格,反映了新加坡历史发展到现在,多元文化已然融合成新的体系,成为某一种文学的、文化的范式。
从1919年5月4日开始,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离开中国很远的异地里,离散华人增添新的文化认识与热情。2019年的今天,新华范式毕竟已将异地转为本地,成就一个不断接受外来元素与整合内在结构的场域,一个从不孤立的岛城。
新华范式的多种形构,体现新加坡主体性的演变。它的变化,在时间上不断在递进。它的繁复,在空间上始终在重组。从王君实的中国魂魄,到胡愈之的归去来兮,苗秀的预留一席,英培安的华文境遇,梁文福的繁管急弦,谢裕民的文学国民,张悦然的跨国流动,以及许多其他在新加坡从事华文书写、进行文化想望的作家文人,他们的语言图像所呈现的精神实质,不但在回应历史的焦虑,而且在肩负地理的沉重。

谢裕民:文学国民
延伸阅读
在《建国》里有一段,讨论人名“建国”“立国”“国民”“美华”“美英”的意思,无不是新加坡语境里的片片断断,组成新加坡主体可堪玩味的错踪与复杂。谢裕民的文学书写,对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侃:
在《誓鸟》的南洋场域里,女性换位成为主角,通过跨越疆界的行旅,消解了男性的历史书写。如果说男性历史书写着重权力与利益的面向,《誓鸟》的女性历史书写则观照情爱和心灵。爱情成为女性行旅的首要理由和唯一准证,情爱深刻地穿越了南洋的种族、性别、宗教的重层界线,解卸身份与政治。
唯有中国的五四,对新华场域产生直接的冲击。它给20世纪初的新加坡华社带来风雷,再次巩固中国的国族意识与爱国情操,对文化与文学意图进行具体的改革。在二战前的那段时间内,新华场域对中国五四的反应是接受的状态,主要的动作是参与中国想象共同体的建构,稍有余力才顾及南洋的社会现实。二战后,新华场域转移政治热情,族群关怀转入新加坡的国家建设。
建国有个弟弟小他六岁,叫立国,今年50岁。是的,1959年建国,1965年立国。一个王姓小岛民以这两个词为儿子命名 ……这种带有狂热爱国意识的名字常令建国觉得突兀与无奈,这样的名字也让人误以为建国爸妈都很有墨水。他们都没进过学校。建国爸说,名字是个教书仔取的。教书仔有一晚被一群“暗牌”带走,建国、立国去。建国还有个弟弟,小立国两岁。教书仔走后,建国爸只好自己为孩子取名,国民。建国爸沾沾自喜,忘了他们姓王,所以弟弟是——王国民。建国还有两个妹妹,美华和美英。建国后来问老爸,万一还有弟妹出世,怎么办?建国爸说,想好了,叫美娥(俄)、美德、美发(法)都可以。建国怎么都看不出,他老子如此有国际观——现在叫全球化。建国爸在开玩笑,美英之后建国便难再有弟妹,建国后来知道是为了——建国,不是人名的建国,是岛民的建国。
应该说,《誓鸟》的寓言更为体现女性作家在新华场域的跨国流动。女性对于南洋记忆的偏重感情的提炼方式,对地理文化和身份政治的流动性的认知,与男性作家侵略性或防卫性的立场有所迥异。
然而,5月4日在别的地方,有别的坐标意义。在英国,1979年5月4日,撒切尔夫人成为史上第一个女首相。开启11年“铁娘子”强硬的领导理念与手腕。在美国,1953年5月4日,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获得普立兹奖,简洁的书写树立美国文学的权威,给世界文学提供某种典范,影响至今。
(游俊豪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那时她们都还是姑娘,像果实一般站在树梢上眺望,海洋不过是块明媚的蓝色花田,没有什么是真正遥不可及的。她们觉得生命那么漫长,由无数黑暗的长夜组成,犹如一条幽仄的回廊,没有尽头。可是姑娘们错了。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轮太阳,每个白昼的光比起前日都要黯淡一些,淙淙的太阳烧得太烈,所以光热很早就耗尽了。
《誓鸟》在中国出版面世,但其创作是在新加坡完成的,灵感来自张悦然留学新加坡经历的大海啸,即2004年12月26日发生的印度洋海啸。张悦然让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在欧洲殖民主义盘踞南洋的年代,女主角是中国女性春迟,在南洋遇到海啸失去部分记忆,回到中国又重返南洋,希望重拾记忆与爱情。
2018年,谢裕民出版长篇小说《建国》,入选《亚洲周刊》当年年度十大小说。
这部长篇小说,剪裁奇特,包含两部分。其一,一个名叫“建国”的主角跟其他人物的互动关系,以及因此展开的故事情节,用了小说的叙事手法。其二,“SG50词典”撰写社会新闻的各种条目,用了媒体的报道方式。这两个部分不断交错,贯穿全书,所达到碎片化的效果,恰恰就是现代的重层语境。在多重脉络的交叠之下,小说里的人民在观察并认知国家的种种,就像万花筒那样,图像可以固定在某一角度,但转换了角度之后又是另一图像。
梁文福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这两方面跟英培安一样。梁1964年生,比英小17岁,属于不同的华人的代际。梁1999年获得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现在是学而优语文中心语文总监、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兼任副教授。1992年,他获得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颁发的第一届“青年艺术家奖”(文学)。
多元性与现代性交响而成的繁管急弦,也可以在诗人周德成的诗集《你和我的故事》里有所呈现。
谢裕民祖籍广东揭阳,1959年生于新加坡,1993年获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颁青年艺术奖,1995年受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他曾任《新明日报》文艺副刊编辑,现为《联合早报》副刊组资深高级编辑,亦负责文艺副刊《文艺城》。他写小说、微型小说、散文。
她2003年从中国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读计算机系,在新加坡求学期间,延续其在中国的文学身份,继续参与中国的文学生产。她198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2001年毕业于山东省实验中学,考入山东大学修读英语、法律双学位。来新加坡前,她已经在中国文坛占得独特的席位,被冠以“美女作家”和“玉女作家”等称号,与韩寒和郭敬明等偶像作家一样,体现中国文学生产走向青春化、商业化、市场化的趋势。她现居北京,专事写作,担任《鲤》系列主题书的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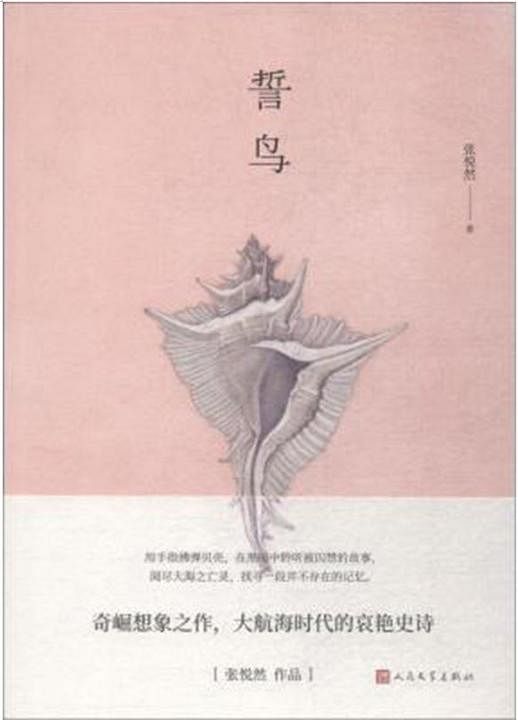
一地,有一地的纪念日。
小说里有一段,写女性到南洋之前对辽阔海洋投射无限的憧憬,以及后来在南洋翻腾着快乐与痛苦的经历:
从新文学到新华文学系列③
1919年5月4日的北京,爆发不寻常的事件。一场青年推动的学生运动,加上许多市民与工商人士参与的一场示威游行,抗议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中懦弱的退让,导致西方列强将山东从德国手中转给日本。
张悦然:跨国流动
《建国》2018年出版前后的这些年里,“建国一代”“新加坡独立50周年”“立国一代”各种概念相继出台,公民因为有不同的背景与经历,所以必然会有不同的想望与想象。《建国》揭示当前新华文学的某种国民性的认知,以及某种再现手法。面对历史的现实与吊诡,这类作家在以更为复杂的文学技巧对题旨进行切入、分割、拼凑,重组真相与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