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临发布会,林康将分享他的编选的理念与过程,作品入选的作家也将出席活动,此外更欢迎读者共襄盛举,与编者、作者近距离交流。
《2018年文字现象》新书发布会
习以为常的世界,一切都那么条理分明,理所当然得叫人安心。然而,生命中、世界上,毕竟还有许多无法言诠的存在,也让人(至少有这么一部分人)无法舒坦地耽溺在一切能解,一切都有便捷答案的明朗世界中,宁愿放下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酷毙作派。这些人愿意卷起衣袖、拉高裤管,到各个未知的幽微角落去搜寻。
壮哉。
不像或不是小说的小说,理应带出来的疑问是小说该像什么或什么才是小说?不像或不是,落到散文落到诗,都理应带出类似的疑问。柯思仁借用布迪厄“场域”观,指出“文学风格与思想的嬗变,文学流派与立场的多元,都连接到文学以外的历史与现实”(见2016年文选序)。文学既然是迷糊跌撞朝幽微处的执着探寻,放在去威权、反众口同声的社会氛围下,文体越界也许本来就不是异常或意外的文字现象。
作为《文艺城》的年度文选,《文字现象》的主场,当然是前者那城。然而,城主在策划之余便撒手放任,把年选文集的“主导权”外放,希望“每年不同编选人,便有不一样的编选风格”,长此以往,“山水相连,便成气候”(杜南发,《2015年文字现象》序)。这是“软体”的一面。另外还有“硬体”的一面,则是年选面对着铁板一块撼动不了的篇幅限制,一如上述。
《2018年文字现象》邀得林康担任主编,收录希尼尔、黄凯德、艾禺、荆云、柯思仁、林高、清哲、潘正镭、杜南发、淡莹、陈志锐、游以飘、吴启基、莫邪、伊蝉、梁文福等作家作品。
“小词典”作者以血泪为史实浇灌前行者的体温,用在当下显得异质的实例,揭示历史的多样性与各种变化的潜在可能,让任何对过去作划一描述的叙事都变得可疑。此外,配合“早报书选”作品的系列对谈,“早报文学节”和“新加坡作家节”本地与外地受邀作家与读者的交流对话,《文艺城》也做了密集的追踪,其中含颇有深度的报道,广泛呈现新华文学场域整体的“外事”与内部活动,打破城里城外的藩篱,“为读者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从另一个角度省视新加坡文学的现状”(借用柯思仁2016年文选序的说法)。
变异的文体跨界徘徊 文学迷糊跌撞的足迹
文学的嬗变和要求众声喧哗的现实
30余年下来,《文艺城》守住城中新华文学的一方乐土。岁月留痕。当年青年不识时务,到此探索然后留下。在这里成长,然后中年,然后“资深”。然而,“城民”整体却未见显著老化,因为即便传统华校消逝,整体华文环境无以复加地恶化,文学被挤到边缘早呈环球化显势,仍陆续有青年一头钻了进来。一代又一代,始终没有断层。
2018年,《文艺城》一开年就刊出谢征达以“新华文学小词典”为总题的小方块,全年92篇,带着读者重返新华文学发展途中的若干重要现场。
2018年《文艺城》发表的评论文章,数量为四年来之冠。年选分两辑收入评论六篇,所涉论述,和文体的变异未必有直接关系,但无不反映文学某种越界或翻转既定秩序的文字现象。
清楚和迷糊交错并行 一个奇特的经验
谢征达《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方修?》,讨论今时今日该如何看待方修。如题目所示,作者把作出正面答复的论述放置在质疑的语境下展开。从黄锦树批评“方修的现实主义观点缺乏文学价值、不利于文学的发展”,到林建国主张应“从宏观客观的视角阅读方修的文学史”,最终作出方修的价值“不只是文学史的编选,也是对理论的思考以及扩充马华文学史脉络”的判断,并提出思考“如何延续方修的新华文学史体系”的新议题。
说“力求清楚”,正是编选过程中这类有别于创作上的“理性”推敲。“力求”该是重点,最终是否弄“清楚”,一时还真说不清楚。
再比较此前三年的体例。杜南发和希尼尔的前后两个文选都按文体分类,柯思仁间中的一个则打破传统依据以主题为纲。原来设想,若效法柯思仁,文选逐年的格式呈ABAB,可让集子的体例连续下来显露某种“格律”的齐整结构,未尝不美。终究没那么往下做,因为在阅读过程中屡屡遭遇冲撞文体分际,甚至施施然穿越界限,面目暧昧难判的作品,为此吸引而改变了思路。编选的取向或意图凸显的风格,也逐渐成形。
周维介以《末代华校高中生实现的文学梦》为题,回溯1977年四名“末代华校高中生”在母语源流教育一片凄风苦雨之际创办《度荒文艺》的始末。《度荒》是一份举着“现代文学”旗帜的期刊,创刊号刊登主编林益洲的《殉道者》,文末附记摆出这样的抗争姿态:“星加坡文坛除了曲解现实主义,使着鲁迅的余威喊喊几句口号的‘写实’作家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次我们举起现代文学的旗帜,若是不能卫道,我们何惧于殉道”。着眼于出现“曲解”和前后加了引号的“写实”的关键词,与其视之为文学的主义或流派之争,不如理解为对当时文坛某种只此一家、非此不可氛围的抗拒,和文体跨界运作的文字现象同属去威权一类。
先驱作家林独步、谭云山、高云览、铁抗;南来文人吴天、洪丝丝、胡愈之、沈兹九;南来作家废名、许杰、郁达夫、刘以鬯、刘延陵、力匡;前辈作家殷枝阳、铁戈、李星可、苗秀、赵戎、韦晕、丘絮絮;卓有贡献的文学副刊与期刊编辑兼作家张楚琨、杏影、姚紫、刘思;早期重要文学平台《新国民杂志》《南风》《椰林》《枯岛》《晨星》《野葩》;影响文学走向的主张与论争马来亚文艺、南洋文化、新兴文学、抗战文学、马华文艺独特性;具独特意义作品《马华新文学大系》《海畔》《十字街头》《怒吼吧!新加坡》《牺牲者的治疗》《在旗下》等,接踵一一闪耀亮相。作者整理拾掇的这些历史片断,为新华文学的前世今生提供了纵深景观,其中不乏可歌可泣的故事,如王君实日据时期护友自杀、洪丝丝被殖民当局驱逐、洪灵菲在香港遭国民党逮捕牺牲,如1950年代民间启动、影响深广的反黄运动。
附设文学副刊,是华文报自中国五四新文学滥觞始并延续至今的传统,成为各地华文大报特有的一个面相,鲜少例外。在本地报业板块发生的系列结构性移动中,先有1983年两大华文报的合并。谢裕民《〈文艺城〉几时出版》(见《2016年文字现象》附录)对此做了相关的回溯记述:合并后的《联合早报》,文学副刊从《星云》到《艺苑》,再到1986年10月20日《文艺城》创刊,从此延续30余年至今。
说了一轮,话题终归要回到文集的编选。
《2018年文字现象》发布会
选集分小说、微型小说、散文、诗歌与评论(两辑)共六辑。此外也附录《阅读版》陈宇昕报道《“伸手抓起,竟是一把鸟声”——回顾30年前洛夫诗引发的论战》一文。
如此“软硬兼施”,编选者貌似享有了设计舞步的自由,实际却仍然是只得戴着镣铐起舞的舞者。要如何舞出风格,不自砸场子,不免煞费心思,因为场子砸了再无法怨天尤人。2015年,杜南发“偏好抒情”;2016年,柯思仁关注“作品产生的文化与社会脉络”;2017年,希尼尔追踪“岛屿。记忆。探索”的足迹。
由于从事这个文集的编选,才有如此一次好一段时间里埋首“城中”的密集阅读,换来一个在力求清楚和刻意迷糊之间交错并行的奇特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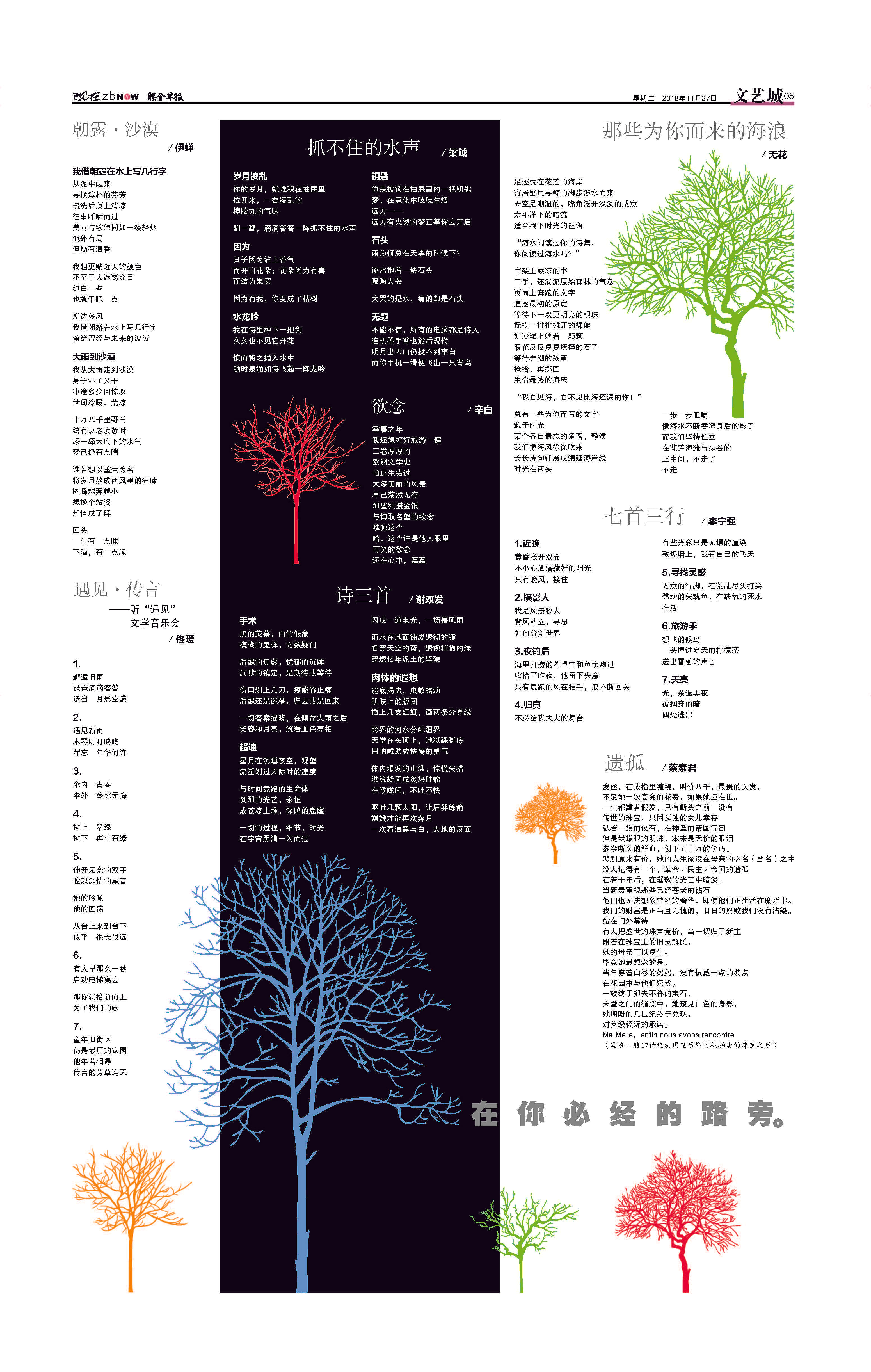
2018年,《文艺城》共出版107期(凡同一天出两个版,按两期计),发表作品555篇(凡一个总题下含数则,按一篇计)。以文体分,全年共发表:诗258篇,散文75篇,小说(含翻译小说)24篇,微型12篇,评论11篇,史料、报道、文讯类书写175篇(谢征达整理的“新华文学小词典”占91篇)。
放眼望去,沿路恣意争妍斗艳的奇花异卉,透露仍存在一群不识时务者不肯轻言放弃的坚韧和执着,彰显(至少对这群人而言)通过文学发现、探索生命与世界未知地带的魅力。在新华文学场域中的这些人,不分城里城外,无论是否受到理解,不管有没有他人理会,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认认真真把自己和自己的志业当一回事。
至于“刻意迷糊”,指涉的是文学的某种特质。文学以抽象符号的文字为媒介(象形文字也还是抽象符号),文字现象之得以形成,并能在习以为常的惯性中透露别致的姿采,端赖人可以转化抽象文字,还原为具体可感的经验或从中领悟到什么的能力。
譬如《楚辞。天问》,明知一时没有答案(甚至长期都不会有一目了然的答案),依然执着。一个个问题追问不休,因为相信,不断追问可向真相趋近。譬如不少拉丁美洲作家,尽管一个个都是生活中立场鲜明的血性汉子,仍主张文学的事,还是要让文学现身说话,交由文学发声。
英培安在早报文学节的主题演讲《小说与真实》,讲述他的小说真实论,以实例指出“小说中的真实不一定只出现在写实主义的小说里,也可以出现在内容怪诞的,超现实的现代小说里”。英培安引述彼得盖伊对马奎斯小说《独裁者的秋天》的分析,认为马奎斯“用文学的想象手法做到历史学家想做或应该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写了一本极具历史意义的小说”,尽管(或恰恰正因为)小说“没有说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虚构,甚至切断可能说明事实的任何线索”。这个论断,使人和马、恩对巴尔扎克,伊里奇对托尔斯泰、卢卡契对卡夫卡最终的评价产生联想,觉察以流派、立场、手法作为定文学作品优劣准绳的虚妄。
王润华为奈保尔辞世,撰写挽文《殖民与后殖民书写的终结?》。针对作为题目的问句,他以“奈保尔把第三世界的透视力与被压制的历史与记忆呈现在帝国主义英语文学里,成为20世纪100本最杰出的英文小说”等例子为依据,给出“文学没有所谓终结”的回答,因为“上面讨论的(这些从事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书写的)作家给我们极大的创作源泉”。王润华结合本土,对我们的“边缘书写”提出“有待超越”的期许,并进一步申说,“其实所有一流的前卫的知识分子或作家,永远都在流亡,不管身在国内或国外,因为知识分子原本就位居社会边缘,远离政治权力”,这样更“可以诚实的捍卫与批评社会”。晞哲阅读流苏《蔷薇边缘》,发现她散文具有“形成一体多面的思考空间”的特点,“读者根据个别层次的眼睛检阅,会收获不同的阅读(悦读)体验”(《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流苏从她研究本地现代主义文学的角度阅读英培安的多个文本(含诗、小说和编辑的杂志),发现英培安文学上“对自己的固执相当坚持,而且贯彻始终”,在“小说人物身上”,在“批判意识浓厚的诗句里”无不如此表现出来,并从中感受到引人“向某个界限跨越”的力量(《英培安的固执及现代主义的二三事》)。
在《文艺城》定名前,《联合早报》文学副刊有从“纯文艺”向“综合性文艺”调整和再进一步综合的经过,定名后也有从每周三出至每周两出等变化(每出一大版,这一点幸好一直没变)。这些端倪,也许透露本地华文报在社会变迁、华文式微、文学旁落的环境下,把附设文学副刊的传统继承下来,未必是那么顺理成章的顺当事。
说编选,说文学。接说文学的平台和文学场域。
从小说传统家族叛逃的异类
晚上7时30分至9时
四年前,联合早报《文艺城》首次推出年度选集,借一年文艺版上的文艺创作,勾勒本地文坛“文字现象”(之一种),此后每年借新加坡书展推出选集。
我一直没有忘却,年少时曾经终夜不寐、忽忽如狂,只为了追求某些片段错落的意象、某些可以抗拒秩序创造幻影的字行。
我真的没有、不可能彻底拒绝破碎、断裂、混乱的诱惑,我真的无法否定碎裂、断裂、混乱其实有其魅力,更有其在生活中存在,搅扰秩序的高度必要。
——杨照《烈焰》序
6月7日(星期五)
改坐等为主动策划组稿 持续焕发生机
《联合早报》文学副刊《文艺城》四年前开始,为所发表作品编辑出版年度文选。杜南发、柯思仁、希尼尔,文选此前的三位主编也许同样有过类似感受,我不晓得。于我(至少于我),由于从事这个文集的编选,才有如此一次好一段时间里埋首“城中”的密集阅读,换来一个在力求清楚和刻意迷糊之间交错并行的奇特经验。
《文艺城》改变坐等作者来稿,采取主动组稿的做法,已行之有年。特别是2017年开始的“一个文本,两种媒介”,其用心明显已经超越“盘活”“炒热”《文艺城》本身,思考的是如何扩大文学作品的回旋空间,和促进发展文学相关。
本地华文大报设文学副刊的传统,总算维系下来。
环境恶劣而不曾断层 壮哉新华文学
杨照阅读札记《烈焰》第22则说,佛斯特总结19世纪西方小说传统规律的《小说面面观》出版后,“每一波新的流行风格,几乎都像是冲着该书而来的敌对反扑”,“一代又一代的小说作者,以该书当反面教材,就是要写出不同于所规定的‘小说’”。这个文集选入的五个小说和五个微型,也都是从小说传统家族叛逃的异类。
新加坡书展主舞台Outdoor Plaza Main Stage @ Level 1
“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诗辨》说得好。“言有尽”,只有另循“意无穷”去着手致力。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在思想和观念说不清楚处摸索。于是,才有了文学。

文学的创作如此,文学的阅读(编选的过程无非阅读的过程)亦当如此。
相对于此,文选的作品容量在60篇上下,面对篇幅只约十分一的局限。十取一,哪怕沿用前两年开始的惯例,每人仅收一篇,如何筛选仍只有“难矣哉”三字可说。在放眼各家如何酣畅(或努力尝试)落实文学理念,在设法维持文选的某种“读者亲和度”(reader-friendly)之间,为求取一定的平衡,不得不作各方考量。来回斟酌的结果是,有时此刻从选录表上删去了下刻再予收回,或者收录了又作删除。如此反复拉锯,直到时限到了只好无奈叫停。
说“刻意迷糊”,重点同样也该是前面二字,说的探寻过程抓耳挠腮的窘态(不见得必然是艰涩的表述),而文学之志在发现和体悟生命,其实是明确和清楚的。迷糊,恰是为了明白,弥补无知或未知的缺憾。
2018年文选的“文字现象”,聚焦点是:变异的文体跨界徘徊。
《文艺城》当然不是新华文学场域的全貌,只是其中一隅。只是,作为本地唯一华文大报的唯一文学副刊,和其他文学平台比较,刊期相对密集,受众面向相对广泛,都是毋庸置疑的。这一隅既占据着特殊位置,自有其一定代表意义。由此折射出来的,多少反映(或不妨想象为)新华文学的某种景观。
没错,要说的就是“总算”。所谓传统,只是古已有之的陈述,不意味着必然或必将继续存在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