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艺术之家 Blue Room
刘震云说:“我心里一震,第一次明白作者是谁,就是一头牛。这里牵涉到一个基本的哲学和数学问题,谁在世界上是重要的?从CNN到BBC,再到NHK,都觉得美国总统、俄国总统和德国总理重要,不但媒体觉得,全世界的人也都这么认为,这些人说的每句话,当天全世界都知道了。也就是说,他们的话语在这个地球上是占空间和时间的,是占面积的;李雪莲想说一句话,20年没人理会她,证明她的话不占面积。正是因为大家都觉得美国总统、俄国总统和德国总理重要,就把李雪莲的喜怒哀乐给忽略,人们的脚步,历史的车轮,毫不在意地从李雪莲的情感上踏过去和轧过去。我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我阻挡不了人们的脚步和历史的车轮,但我是一个作者,可以写字——文学的作用,就是要把世界、CNN和BBC忽略的东西,一点一滴打捞出来。当全世界都觉得这个妇女不重要时,我觉得她重要,当李雪莲的心事无处诉说时,我作为一个倾听者坐到她身边。现在我的书有20多种文字,当我把她的肺腑之言通过文学告诉中国读者和其他许多民族读者的时候,更多的倾听者也坐到这个在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人身边。这就是肺腑之言的力量,文学的力量,也是一个作者存在的价值。”
主讲:刘震云、孙爱玲、英培安
刘震云的小说《手机》《温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和《一句顶一万句》等被改编成电影,谈到小说和电影的关系,刘震云有自己的看法:“小说和电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动物’,如果比作吃饭,电影重视的是已经端到桌子上的一盘菜,要色香味俱全;小说重视的是在厨房剥葱剥蒜的过程,及肉和菜下油锅时滋啦的声音和腾出来的火苗。也就是,电影重视的是动作和台词,小说重视的是心理描写;电影重视的是这件事本身,小说重视的是这件事如何来的。”
刘震云接着去意大利的米兰,恰好第二天米兰大教堂有弥撒,于是他去米兰大教堂的弥撒。他说:“教堂的大主教——已经是个80多岁的老人慈祥和步履蹒跚地走出来的时候,我在心里说,老人家,我认识你呀。这时我后悔在写作时对人物思考得不深不细,如果当时我能想到法国男士说的这一层,作品里的人物,一定会走得更远。”
冯小刚的电影
去年冬天,刘震云到法国交流,在巴黎第七大学,一个法国男士说,他读了法文的《一句顶一万句》,对这个意大利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唏嘘感慨良久。他问刘震云,可知道这个传教士妹妹的那个八岁的孩子如今在干什么吗?
却叫人看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可理喻。

他说:“写一部作品的时候,都想把它写好。但作品出版后回过头看,或者经读者朋友指出,每部作品都会有缺憾。”
他说: “去年春天这本书出荷兰文时,我去荷兰配合出版做推广工作,一次在书店与读者交流,一个荷兰女士说,她看这本书从头至尾都在笑,但当她看到李雪莲与所有人说话,所有人都不听,只好把话说给家里的一头牛时,这个荷兰女士哭了。接着荷兰女士说,当世界上只有一头牛听李雪莲说话时,其实还有另外一头牛也在听李雪莲说话,就是这本书作者。”
刘震云与导演冯小刚是大家公认的好搭档,说到冯小刚爱拍他的小说的原因,刘震云说:“其实我的小说不适合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因为影视的基本要素是作品的情节性要强,我的小说在这方面很差。在中国大陆,没有很多导演要改编我的小说,冯小刚导演是例外。他对我说,他看重的不是影视作品表面的要素,是作品背后的含义。譬如《一地鸡毛》中大和小之间的关系,《温故一九四二》用幽默的方式在写饿死300万人的悲剧,《我不是潘金莲》啼笑皆非的荒诞。冯小刚与众不同,由于他见解的不同,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之中,刘震云公认为讲故事高手,不但文字功力高,作品十分接地气,充满生活气息,小说表面像写了一个个荒诞的故事,却叫人看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可理喻。
刘震云早期的经典之作《一地鸡毛》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世纪世界百部文学经典”之一,说起这部30年前的作品,刘震云说:“《一地鸡毛》主要写的是大和小的关系。小林是中国一个普通的小市民,全世界的人都以为八国首脑会议重要,但小林以为,他家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重要。这是这篇小说的哲学基点。”
刘震云最新长篇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去年底问世后,同样引起很大的好评。这是一部可以一口气读完的小说,小说最特别的是,故事中四个人物,包括农村姑娘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他们素不相识,但小说家却有本事让四个人物串成故事。
刘震云还和女儿刘雨霖合作拍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一般人也许认为,父女合作更能取得互动,但刘震云说:“一个导演要改编一个作者的小说,父女关系已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为什么要改编这部作品,及如何改编这部作品。其实,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也不适合改编电影,因为这部作品的时间跨度太大,从上个世纪初一直到现在;还有作品里人物众多,有名有姓的人物有100多个,电影的主人公不能超过两个或三个。最后她的处理办法,是选择其中几个章节。我想,这是一个有效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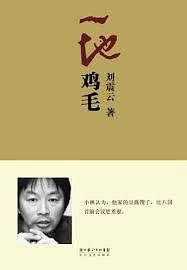
中国小说家刘震云是讲故事高手,他的小说表面像写荒诞的故事,
今年4月,刘震云获法国文化部授予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授勋辞说:“您的作品在中国读者中取得巨大成功,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广受国际读者的欢迎。您开创‘现实魔幻主义’,一些国外评论家认为您是‘中国最伟大的幽默大师’……”

刘震云即将于11月初到新加坡参与作家节,他在北京接受《联合早报》电邮访问时,对“幽默”提出看法:“幽默有几个层面。首先是语言的幽默,作者的叙述语言很俏皮。第二是作品的细节和情节很幽默,譬如黄鼠狼给鸡拜年——黄鼠狼是吃鸡的,却在过年提着礼物去看鸡,其野心昭然若揭。”
日期:11月3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4时30分至6时
作者存在的价值
在刘震云看来,电影要求叙述节奏要快,如一条奔腾的河流,不断要穿越不同的地方,遇到地势有落差的地方,就成瀑布。但小说是大海,大海表面的浪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海底部的涡流和潜流,及潮涨潮落跟太阳和月亮的关系。如果比作动物,电影像在田野上快速奔跑的豹子,小说像大象,走路慢吞吞的,边走边想些什么。
刘震云说:“我一时回答不上来,因为这个孩子在作品里没有正面出现,只是一个收信者。这个男士告诉我,他现在就是米兰大教堂的大主教。我听了这话,心里一震。因为他想得比我远,也比我深。”
但我是一个作者,可以把世界忽略的东西,一点一滴打捞出来。”
刘震云认为,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故事和人物结构的幽默。他以近年来的扛鼎之作《我不是潘金莲》为例子,小说主人公李雪莲是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为了纠正一句话“我不是一个坏女人”,开始她的告状生涯。从村里告到县里,从县里告到市里,最后告到北京,花了20年功夫,这句话还是没有纠正过来。一开始还有人同情她,后来她的告状成了笑话。20年间,她把自己的悲剧演成喜剧。
每部作品都有缺憾
受访者提供照片

人物结构的实验
刘震云的小说
被冯小刚搬上银幕,备受注目的《我不是潘金莲》也让刘震云感受到文学的力量。
刘震云说:“四个人本不相识,相互不在一个县,不一个市,也不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穿越大半个中国打着了。这种情形在我以前的作品中没有过,以前我书中的人物关系是紧密的,这回书里的四个人素不相识,主要是写人物关系的空白,是一次人物结构的实验。
他说:“我是一介书生,阻挡不了人们的脚步和历史的车轮,
刘震云说:“现在评论家把我的作品定位为‘现实魔幻主义’,大概跟这种结构上的幽默有关。”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提及这部小说,刘震云却谈到对自己创作的遗憾。
幽默与现实魔幻主义
至于何谓“吃瓜时代”,刘震云说,“吃瓜”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网络用语,指“看热闹”“围观”的意思。网络为何把“吃瓜”和看热闹、围观联系在一起,一开始他也想不明白,后来揣度,大概是众人看到别人倒霉,像吃西瓜一样甜在心里吧。大家爱“吃瓜”,是因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在舞台上已没落,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幕搬到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这是“吃瓜”的最好的时代。
刘震云说:“《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李雪莲一层层告状,因为阴差阳错,撤了一批官员,包括县长史为民。20年后,史为民成了一个厨子,他坐火车到东北看亲戚,回来在北京转车买不上火车票。因为赶上了春节,大家都急着回家,这时史为民急中生智,用李雪莲告状手法,在火车站举起一个告状的牌子,马上被警察捉住,接着把他押送回老家,他的阴谋成功。他急着回老家,仅仅为了打一场麻将。”
刘震云说:“以前的主人公是作品里的人,如《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温故一九四二》中的300万灾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和牛爱国,《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这回主角不是在书里出现的四个人,而是没出场的吃瓜群众。也就是,这回写的是没写的那部分人。书里的四个人痛不欲生,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却乐不可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还有一部分吃瓜群众是谁呢?就是看这本书的读者朋友。看他们读了这本书,对作品中的人物如何幸灾乐祸。”
话虽如此,刘震云显然满意与女儿的合作,他说:“她认为好电影里不应该有导演的影子,不应该有摄像机的影子,不应该有演员的影子,有的只是剧中的人物和他们的情感。这跟我对小说的认识差不多。相同的认识,是合作的基础。她还告诉我,《一句顶一万句》可以拍成十部电影。我等着她付给我剩下的九次的版权费。”
刘震云举《一句顶一万句》说:“书中有一个意大利神父,上个世纪初到我的故乡中国河南延津县传教。他本名希门尼斯·歇尔·本斯普马基,中国名字叫詹善仆,延津人把他的名字简化成老詹。老詹来延津时不会说中国话,转眼40多年过去,会说中国话,会说河南话,会说延津话;老詹传教传了40多年,只发展八个徒弟,但他仍锲而不舍,风里雨里,骑着菲利普自行车,每天去各村传教。由于心里的教义无处诉说,他每天给远在意大利米兰的妹妹的一个八岁儿子写信,诉说他对教义的热爱和理解。那个八岁的孩子,便以为老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士,他在世界的东方,起码有几百万信徒。”
还有受众,电影是许多人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观看的,小说是一个人读,有点像两个人在灯下谈心。还有篇幅,通常电影时长90分钟或两个小时,小说可以随着作者的思绪无限延长。我适合写小说,因为我走路慢,像大象,我不懂电影,那是一个专门的行业。因为我不懂电影,我只是有小说被改成电影,是作品跨界,不是人跨界。电影拍得好,是导演的功劳;拍得不好,可能是我的小说没有提供足够拍摄一个好电影的内容吧。”
讲座:社会与中文现代小说
有趣的是,刘震云说:“现在一地鸡毛已成了中国大陆一个‘成语’,但大家望文生义,形容的内容指向已不是小说原来的主旨,变成混乱加糟糕的意思。如中国足球,一地鸡毛;八国首脑会议,一地鸡毛。这也是文学和生活之间的荒诞和幽默吧。”
